2021-06-21 14:55:19 來源:中國周刊

作者李忠夏: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本文來源:《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數字時代是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以數字化的信息為基本單位所進行的社會交往。信息、數據、互聯網構成了數字時代的三駕馬車。信息的數據化,以及基于互聯網所產生的數據進行運算并加以應用,成為數字時代的基本特征。信息的數字化是一場深刻的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并隨之帶來了法律上的變革。數字時代,隱私權得到更多的關注和研究,但這一問題卻遠未得到妥善解決。一百多年前沃倫和布蘭代斯對隱私的經典界定能否適應數字時代的新形勢,不無疑問。即使將隱私擴展至個人信息控制,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隱私與個人(信息)自主權之間畢竟存在一種隱微的差異。數字時代,隱私究竟重要在何處?承擔了何種社會功能?何種事務可以被納入隱私的范疇?應在多大程度上保護隱私?諸如此類的問題,仍有重新被討論的價值,并亟須在憲法層面對隱私進行體系化重構。
一、隱私: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區隔的結構紐帶
隱私是社會性的。如果不是在社會當中,隱私就毫無意義。可以設想,荒島之上的魯濱遜并不需要隱私。隱私從一開始就服務于人類在社會中更好地生存,具有社會功能。隱私是個人在社會之內的隱匿或者逃遁。正是由于社會復雜性提升,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個人在社會之內對社會的逃離才顯得越發重要。隱私是界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重要媒介。在數字社會,溝通發生了重大改變,私人領域公共化的現象更加嚴重。這使得隱私當中所蘊含的人格性及其社會功能更需得到彰顯,其一直以來差強人意的保護狀況亟須得到改善。
隱私是人格性的直接體現,并承載著“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區隔”的社會功能,這一功能在數字社會當中尤為重要。人類之所以會產生社會系統,根源在于人與人之間在心理層面上的“高度不可溝通性”。正是因為心理的不可見,才從心理系統當中“涌現”出了社會系統。在社會溝通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人(Mensch)與人格(Person)的分離。在社會系統當中,人所呈現出來的并非是將所有心理狀態都表露于外的“真正的人”,而是根據其外在表現所呈現出來的人格體。盧曼認為:“人格的形式只服務于社會系統的自我組織,并通過對參與者行為可能性的限制來解決雙重偶聯性問題”,人格是“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的結構紐帶”:借由人格,人可以進入社會當中,而不是將自己的心理徹底暴露于社會;通過人格的緩沖,可以保護個人實現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適度區隔。
在人與人格分離的基礎上,人的自我描述就顯得尤為重要。“自我描述(Selbstdarstellung)是使人與他人進行溝通時變為人格體,并因此在其人性(Menschheit)中加以構筑的過程。如果沒有成功的自我描述、沒有尊嚴,他就無法應用其人格性。如果無法進行充分的自我描述,他就無法成為溝通的一方,并且他對于系統要求的不當理解就會將他帶入到瘋人院當中”。根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界定,人的“自我描述”,本質上意味著人的自主權和自我決定權,即可以自主決定自己在社會中所呈現出來的面貌。
到了數字時代,人與人格的分離更加明顯,并且從社會的人格當中又分離出互聯網人格。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呈現出的人格,與互聯網中所呈現出的可能截然不同。如果說前近代社會是熟人社會,進入到工業化時代之后,熟人社會轉型為陌生人社會,那么今天的互聯網社會就是超大型的“隱身陌生人社會”。互聯網社會當中,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隱身化”改變了溝通的生態,體現了網絡溝通既隱匿又公開的雙重特點:一方面,網絡行為具有很強的隱匿性,人們的網絡行為往往隨意性很強,網絡謠言層出不窮,語言暴力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網絡中的“人肉搜索”功能強大,讓人無所遁形。這導致互聯網當中,人們既肆無忌憚又謹小慎微,不該發表的言論大行其道,該發表的言論卻顧慮重重。網絡中的言論呈現出很強的攻擊性,對真正的言論和隱私都形成了威脅,言論本身反而壓制了言論。
數字改變了人格的存在形式,數字化和虛擬化導致個人在現代社會是具有雙重維度的存在:一重是現實中的存在,另一重則是數字化的存在。數字社會加劇了人格自由展開的“恣意性”。在社會當中,人已經實現了與人格的分離。進入互聯網社會之后,又進一步實現了人格自身的分裂,即線上的數字人格與線下的現實人格的分裂。這二者同屬社會人格,但數字人格相較現實人格,更少社會約束,更具有恣意性,可以肆意地展開謾罵、誹謗、造謠、攻擊等行為。這些行為或許平時隱藏在內心深處,如今借助網絡得到釋放,從而使網絡中的數字人格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更接近“真實的”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數字人格的展開就既需要保護又需要加以限制。保護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能夠更加自由地發表各種見解和言論。限制的目的則是要限制互聯網中肆無忌憚的謾罵和無所不用其極的隱私揭露,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言論的系統性壓制。
數字時代,互聯網加上信息的數字化,使得信息傳播和隱私受侵害的成本大為降低,而人格受損的后果卻更為嚴重。個人的信息——無論是否具有私密性——經過互聯網的發酵,都可能給個人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和負擔。信息數字化會使得原本不會留痕的即時溝通,可隨時隨地通過數字方式留下痕跡,并傳播到網絡等公共空間。未經同意的截屏、拍照、視頻可以隨意被發布到網絡空間,每個人的行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通過互聯網得到放大。隨時隨地的信息網絡化,使人們的人格(隱私、名譽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私人場合的言論、不知情下的形象、經過剪輯加工的場景、通過偷拍而杜撰的故事,都可以在網絡中形成輿論風波,進而給當事人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隨時隨地的信息“留痕”,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一分為二:一方面,它確實能夠提高監督的力度;另一方面卻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人們由于擔心被留痕而不敢發表意見,進而影響到言論自由的功能實現。這種提高監督能力的益處,也可能因為公權力機構的強勢而大打折扣,即真正給公權力帶來影響的“信息”可能會被壓制,甚至給言論發表者帶來不利后果,比如本屬言論自由的批評聲音,卻可能會被定性為“侮辱”。這使得真正的言論自由功能反而無法實現,而信息肆意發表所帶來的負面后果卻不斷強化。互聯網的此種悖論式現象,解決的根本之道在于:規范網絡言論、強化隱私保護。規范言論,并不是要對言論自由課以更多的限制,而是要從中識別出真正的言論自由。通過憲法機制更好地發揮言論自由的功能,即政治性言論和價值性言論的多元化表達,而非鼓勵網絡中的言論暴力。隱私保護的加強,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有助于消除網絡暴力、增進言論自由。
由此可見,網絡上的信息留痕,導致溝通的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格、言論、監督、網絡暴力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何種言論屬于“批評建議”(《憲法》第41條)、何種言論構成了對人格的侵犯、何種言論會造成對言論本身的壓制,在今天的數字社會尤其需要加以研究。這就需要對憲法中的各種概念進行澄清,隱私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只有隱私得到保證,數字時代更為有序的信息流通才成為可能。在我國,憲法中并無隱私之規定,對于隱私的保護是否有必要上升到憲法層次,這是首先需要討論的問題。其次需要探討的是,如何對隱私權進行憲法教義學上的規范建構。最后,需要針對數字時代的特征,對隱私權的保護范圍進行界定,從而使隱私權的社會功能得以更好地實現。
二、憲法隱私權的建構必要性及保護范圍
在我國,《民法典》當中明確規定了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權。在私法已有規定并對之加以保護的情況下,憲法是否仍有規定之必要,是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隱私憲法保護的必要性在于以下兩點。(1)防范國家公權力對隱私的侵害。眾所周知,民法所針對的是私主體之間的權利侵害,但就傳統而言,對于隱私的威脅主要來自國家公權力,比如非法搜查、監聽、監控等。在數字時代,國家對隱私的侵入和對個人信息的搜集更是變本加厲,隨著技術的發展,其侵入的方式和能力都在不斷增強。(2)構建輻射法律體系的“隱私”價值。憲法對基本權利的規定,其功能不僅在于可以對國家公權力加以防范,還在于基本權利作為“客觀價值秩序”具有輻射整個法律體系的效力。作為基本權利的隱私權同樣也不例外,應該通過憲法中的價值規定,對刑法、行政法、民法等領域的隱私保護加以統合。在數字時代,個人信息本身就具有獨立的保護價值,而不能僅僅停留于私密信息層面。但實踐當中,對個人信息/數據的保護,仍然與隱私密切聯系到一起。在歐盟,對個人數據和信息的保護,仍然是在隱私權的保護框架之中。就此而言,憲法層面對于隱私的規范建構就顯得尤為必要。
探討完隱私憲法保護的必要性之后,接下來需要探討的是:如何在憲法層面構建隱私保護的規范體系,以及如何確定隱私權的保護范圍。
(一)隱私權的憲法建構:未列舉的基本權利
憲法中并未規定隱私權這一事實注定了,要發展憲法中的隱私權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修憲;其二是解釋。鑒于修憲的困難,于解釋學層面通過“未列舉基本權利”的學理建構發展出隱私權,是一條更為現實可行的路徑。
未列舉基本權利的理論基礎來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憲法實踐,在德國則通過對《基本法》第2條第1款“人格自由發展”的解釋,發展出“一般行為自由”作為未列舉基本權利的兜底條款。無論美國還是德國,通過判例和解釋發展出“未列舉基本權利”的原因是:社會變動不居,制憲者不可能預計后世所有的社會變化,憲法權利的保護應與時俱進,其范圍也不應拘泥于文本上所明確列舉的那些權利。18世紀末,美國的制憲國父們顯然無法預見到現代網絡社會使得每個人都無所遁形。顯然,1949年德國《基本法》的制定者們也無法預見這一點。“八二憲法”的修憲者們,對即將到來的科技發展和互聯網革命同樣毫無概念。未列舉基本權利的必要性,源于憲法文本與社會變遷之間的內在緊張,由此需要憲法文本保持其解釋上的開放性,這也是“建構”一詞的本義,即通過解釋進行創造。在我國,《憲法》第33條第3款“人權條款”,可以作為“未列舉基本權利”或者“一般行為自由”的規范基礎。由于隱私的人格屬性,《憲法》第38條的“人格尊嚴”條款,也可以作為隱私權的規范基礎。“人權條款”+“人格尊嚴”可以共同構成憲法隱私權的規范來源。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從“未列舉基本權利”的角度證成隱私權之外,還需要從憲法體系的角度對隱私權進行規范建構。從憲法文本來看,《憲法》第39條住宅不受侵犯、第40條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及第38條的人格尊嚴條款中都蘊含了隱私的價值。由此,需要結合這些條款,對隱私的不同面向進行體系化的研究,這些條款是共同構成隱私權的權利束。如何依托這些條款,形成隱私的不同功能層次,就需進入隱私權保護范圍的研究當中。
(二)隱私權保護范圍中的爭議
要界定一項基本權利,首先要對其保護范圍進行界定。所謂保護范圍指的是:何種行為方式(比如自由表達意見)、何種屬性(比如未受過刑罰處分的)、何種情境(比如不受干擾地待在自己的住宅中)、何種法律地位(比如對某物的所有權)或者法益(比如生命或者身體不受損害)應該在基本權利的干預中加以保護,從而確定防御權的適用范圍。對于基本權利保護范圍的界定,主要應從傳統解釋方法入手,討論某項基本權利的“事務邊界”,并在特定情況下,通過目的考量對之加以限縮。比如人身自由的保護范圍,就需要從發生史角度,將之限定于通過“逮捕”“拘禁”等物理性強制措施加以限制的情況,而非擴展至出國等出行自由之上。
對保護范圍的確定,首先要看憲法當中是否對之進行了內在保留,比如“正常的宗教活動”(《憲法》第36條)、“有益于人民的創造性工作”(《憲法》第47條)及憲法雖未明確規定,但顯然應該滿足的“和平”集會,都屬于對保護范圍的內在約束。在這里,“正常的”“有益于人民的”,其內涵都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接下來,就需要從文本的字面含義,對相關概念進行解釋。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對于某一概念的理解,與法律層面的規范理解并不能完全重合。法律概念通常在生活概念的基礎上,附著特定的目的,如《憲法》第39條規定的“住宅”就呈現出這種日常概念與法律概念相分化的特征。
從字面理解,隱私包括隱和私兩部分內容。無論是沃倫和布蘭代斯的界定,還是普羅斯的界定,乃至后來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采納的界定,以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界定,都離不開這兩個方面。波斯納將之總結為“秘密”“隱遁”“自主”三部分內容。“秘密”和“隱遁”是隱的方面,“自主”則是私的方面。爭議在于,“隱私”的這兩部分內容是并列的,還是“私”要受到“隱”的限定。在有的學者看來,私人事務的“自主決定權”(如對于墮胎、性取向的自主決定),屬于政策領域,不應該納入隱私范疇。但另外有學者則從“自主決定權”出發,將隱私擴展到一切對個人信息的控制領域。由字面理解所產生的爭論,恰在于人們對于現實所出現問題的不同診斷方案,這就需要離開字面,轉向隱私的社會功能,從而化解其中的爭論。
前文所述,隱私的社會功能在于在社會當中保障個人能夠“隱”于社會,并掌控自己的“個人事務”。在今天的復雜社會當中,人們對于隱私持兩種不同的態度,其理由卻都是基于“社會”:一種觀點認為,隱私需要得到更加嚴格的保護,個體隱私的保障,可以使個體能夠更加安心地參與到社會(如隱私對于言論自由的促進作用);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今天的信息社會當中,出于信息傳播的考慮,應該適當放松對隱私的保護,以利于信息的傳播。鑒于數字社會,信息爆炸且容易被公開,人們傾向于將隱私擴展到一切個人信息的控制層面。但圍繞個人信息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護,人們卻爭論不下。對個人信息保護過多,就有可能阻礙數字時代的創新,對個人信息保護過少,則可能使個體面臨各種侵擾,甚至面臨安全問題。
從隱私到個人信息的擴張,對非私密性個人信息的保護,目前主要是通過隱私概念的擴張來實現。美國和德國都將隱私擴展為個人自主之上來實現對個人信息的擴張性保護。中國的實踐則相反,《民法典》將隱私概念限縮,在隱私之外另行創設個人信息權。個人信息之所以具有獨立的重要性,根源在于,在數字時代,看上去不具有私密性的個人信息最終仍可能會泄露個人隱私,給個人私生活帶來困擾,其本質目的仍在于保護隱私。隱私與個人信息的二元劃分,是風險社會的后果,具有典型的風險社會的特征,即當下的決定總是存在著造成未來損失的可能性。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主要源自侵害個人信息可能會帶來的潛在的對隱私利益的侵害風險,是一種基于風險不確定性的預防性保護。隱私與個人信息的二分不能成為真正的毫無關聯的二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也要建立在潛在的隱私利益的基礎之上。目前隱私與個人信息二分的私法安排,在實踐中產生了問題。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在判決中認定,微信的好友關系不具有私密性,不屬于隱私,因而不應給予法律保護。這忽視了這種個人信息(包括作為元數據的位置信息)在私法中具有獨立的保護價值,且具有潛在的隱私利益。
為適應時代的發展,隱私在今天更多與個人自主聯系到一起。傳統隱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不受打擾;二是隱藏信息。這二者當中都包含了“自主性”。不受打擾意味著對私人空間的自主性,隱藏信息意味著對個人信息的自主控制。但這兩者當中所包含的自主性,是一種消極的自主性,即不受侵擾的自主性。還存在另外一種積極的自主性,類似于“一般行為自由”,像生育自主、姓名自主、個人自主等,都可歸為這一類。這種積極的自主權,模糊了隱私的邊界,在波斯納看來,這不免將隱私的真正內容排除在外了。
鑒于個人信息與隱私之間這種模糊的關聯:將個人信息過窄限定于私密性之上,在數字時代,可能不利于隱私的保護;將隱私擴張于所有個人信息控制之上,則可能使隱私丟失其本質屬性,并且不利于信息的傳播與交流。有鑒于此,有學者指出,可以將個人信息納入財產權的范疇。但個人信息的財產屬性,只能是在自我決定權基礎上的一種延伸,而不能成為其本質屬性。個人信息保護的人格屬性與激勵信息流通的財產屬性是兩種邏輯,不能混淆。
(三)隱私權保護范圍的規范界定:隱私的層級保護
是否應該將隱私擴張到一切個人信息之上?對個人信息的保護究竟應該到何種程度?這兩個問題決定了今天數字時代隱私權的保護范圍。如果從隱于社會的功能視角來看,隱私當然應該將個人信息的自主控制考量在內。在數字時代,個人信息被各種搜集、分析和利用。令人困擾的不僅包括私密信息被披露,還包括任何個人信息均可能被任意地公開化。個人信息一旦在網絡上發酵,就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持續給個人帶來困擾。此外,大數據的運用也打破了傳統上人們對私密信息的理解,各種公開信息的疊加很可能會暴露個人的私密。所有這些,都有理由將隱私擴展到個人信息之上。從這個角度來說,將隱私擴展到個人信息的目的,也是為了在數字時代更好地保護個人的“私密”。只有與私密有關的個人信息才在隱私的保護之下。只是由于數字時代技術的發展,人們事先并無法確定哪些信息與隱私高度相關,故而才傾向于盡可能拓寬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這也意味著,并非所有的信息都絕對在個人控制之下,一些相對公開的個人信息(如公開于網站之上的個人信息),則可以進入到公共領域。
從這個角度來說,隱私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1)私密空間;(2)私人事務/私密信息;(3)個人信息。結合隱私的社會功能,以及我國的憲法文本,可以對之進行“層級化的規范建構”。
在數字時代,社會系統中兩個奠基性的要素是隱私與信息。沒有隱私,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同一,社會系統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信息,數字時代就失去了根基。隱私與信息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張力,隱私拒絕公開,信息在數字時代,則天然具有公開化的傾向。在這一背景下,隱私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保持個體與社會的區隔,在人與人之間聯系更為緊密、更為開放、更加公開化的互聯網社會中保持個人的私密性;另一方面,隱私使真正的溝通成為可能,只有在隱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可避免因寒蟬效應而導致的溝通障礙。對隱私進行保護,是為了使個人信息在數字時代得以更好地流通。
隱私作為溝通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的人格,其最核心的保護價值在于:人有權使自己與社會適度區隔,并決定自己在社會當中所呈現出的人格。由此可見,對于隱私的保護,端賴于某項事務與個人心理的相關程度。隱私的保護層次,是一種逐漸擴展開來的“差序格局”。根據與心理層面的相關度,而逐漸輻射出去。越靠近心理層面,保護程度越高,輻射至外圍,則保護程度相應減弱。據此,就可對隱私的不同類型展開分析。基于與心理的相關度,可推知不同隱私的保護程度。與個人關系最緊密者為私密空間、私密活動和私密信息。在這其中,純屬個人私密者,應具有最高的保護程度。涉及家庭、伴侶、朋友之間的則次之。以此類推,公開程度越高的空間、活動和信息,則保護程度越低。純屬個人事務的私密性,與溝通中的私密性,同屬最高保護程度的隱私范疇。二者的目的都是為了溝通的順利進行。前者是擔心個人私密被曝光,而間接影響到個人在互聯網中的言論;后者是擔心溝通內容被泄露,而直接影響到溝通本身。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都應該嚴格受到保護。與私密性并不直接相關的個人信息,但可能涉及隱私利益者,也應該予以保護,只是相較于私密性程度較高的隱私而言,其保護程度相對較低。換言之,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并非完全獨立于隱私,而是要納入隱私的范疇,只有與隱私利益相關的個人信息才值得保護。
結合我國的憲法文本,這種層級式的隱私保護也可以找到其文本基礎。在我國憲法中,隱私雖未被明文加以規定,但卻散見于不同的憲法條款當中。如《憲法》第39條的“住宅不受侵犯”和第40條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兩個條款分別涵蓋了隱私中的私密空間和溝通中的信息隱私。隱私中的其他內容,如私人事務的自主決定、通信之外的私密信息保護和其他的個人信息保護等,則應通過《憲法》第38條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結合第33條第3款的“尊重和保障人權”,推導出“一般隱私權”,對之加以保護。上述條款,文本當中規定了程度不同的限制性規定。對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文本中設定的是一種“加重法律保留”的限制性規定;對于“住宅不受侵犯”,則符合簡單法律保留的要件即可,其限制形式僅限于“搜查和侵入”;對于“一般隱私權”而言,如果對它的干預涉及“侮辱”“誹謗”“誣告陷害”等情形,則需一律禁止,除此之外,符合簡單法律保留的要件即可。
上述憲法條款在1982年修憲時有其自身的考慮,甚至可以追溯至更早的1954年憲法第90條的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其制定之初雖然也包含了特定的“隱私”利益,但與今天隱私的重要性以及隱私所遭受的深度威脅相比,顯然遠遠不夠。彼時,隱私的利益僅限于住宅和通信,在今天看來,已經落后于時代。因而,不能嚴格恪守原旨主義,僵化地探尋“制憲者原意”,而是需要結合今天的社會情勢,對之進行教義學上的解釋更新。
三、憲法隱私權的規范體系
在解釋學層面上,憲法隱私權的體系建構,關鍵在于:(1)如何通過解釋學,將私密空間與住宅條款結合到一起,從而突破傳統住宅的語義理解;(2)通信的保護范圍需要一定程度的擴展,并厘清“通信秘密”的內涵;(3)住宅和通信之外的隱私利益需要得到規范上的保護,并與住宅和通信中的隱私保護進行類型化的安排。
(一)私密空間:住宅的界定
如果從1954年制憲和1982年修憲的社會背景來看,“住宅”是個人私密空間的主要載體。在當時,商品經濟尚未展開,租房等形式并不多見,人們對于住宅的理解也并未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但到了今天,隨著生活形式的多元化,私密空間的承載形式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得到極大的拓展。旨在保護“私密空間”的“住宅不受侵犯”,也需要擴大其保護范圍。自“延安黃碟案”以來,圍繞“住宅”所產生的爭議就一直存在。“前店后宅”形式的房屋算住宅還是店鋪?小轎車算不算是住宅?房車算不算住宅?商場的試衣間屬不屬于私密空間?租住的房屋、大學生宿舍能否納入住宅的范疇?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亟須教義學上的回應。
“住宅不受侵犯”是一種與住宅高度相關的人格保護。住宅需與“私密空間”聯系到一起,并根據不同住宅形式其私密性程度的不同,進行類型化的處理,給予其不同程度的隱私保護。這種依據類型所區分的保護強度,也要視住宅形式的功能來界定。住宅保護的目的在于,在不同形式的生活空間當中保持其應有的私密性。根據功能定性,個人自有的房屋是傳統意義上的住宅,私密性最強。租住的房屋應具有同等私密性,以安全為由隨意進行的檢查也不能被允許。前店后宅的店鋪、學生宿舍等同樣如此,都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私密空間,但可以視其功能在符合法律保留的前提下,給予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對于試衣間而言,其功能在于試衣,超出其功能的事項則不能被允許。
從《憲法》第39條的規范結構來看,對住宅不受侵犯的限制規定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這一限制性條款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1)從“禁止非法”中可以推導出簡單的法律保留,即對住宅的搜查和侵入可以通過法律或者基于法律的形式作出;(2)對限制之限制,即并非只要符合法律保留的限制都被視為是合憲的,還需要對法律的限制性內容保留憲法判斷的空間。限制要符合比例原則,要根據住宅的類型合理界定搜查和侵入的程度。以小轎車為例,對小轎車的檢查應該以交通安全為必要性,符合法律的授權方可允許。對于房車的檢查,同樣如此,如果相關規范性文件規定可以超越交通安全的事由對之任意檢查,則需要接受憲法的審查。
在數字時代,住宅受到的威脅不僅來自各種形式的物理侵入,還包括各種數字方面的侵入,如監聽、監控、網絡侵入等。各種形式的數字侵入,如超過特定的功能范疇,應受到嚴格的限制。在“物聯網”時代,各種家用產品都可以接入互聯網,實現家居的智能化,對其進行遠程控制。但這種智能化也加大了住宅被第三方監控的風險,其在住宅之內所捕捉的視頻等信息,如果被公之于眾,同樣構成對住宅的“非法侵入”。
(二)溝通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條款的規范解釋
1. 通信的本質:服務于溝通
由于“通信”擁有了各種各樣的數字化形式,《憲法》第40條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護條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與住宅不受侵犯條款相同,“通信”條款同樣需要進行解釋上的重構。根據1954年憲法規定,住宅條款與通信條款是合二為一的,1982年憲法將之拆分為兩個獨立的條款。這表明,二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都涉及隱私利益。根據1982年修憲時的討論,“通信”不包含電話,而只包括書信、電報等以紙張為媒介的通信。然而需注意1982年時的社會環境,在當時,電話尚不普及,非普通人所能使用,對電話的監聽實際意味著對官員等特殊人群的某種監督,這與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主要以保護公民為目的的主旨并不相符,這應該是當時將電話排除在通信之外的主要原因。
就此而言,對何謂“通信”就需重新加以界定。對“八二憲法”的解釋,尤其應考慮憲法變遷的要素,蓋因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歷經五次修改的“八二憲法”本身也已發生了重要變化。但制憲者原意又非完全可棄之不顧。制憲者制定通信條款的規范目的是為了保護“私人間的信息交換”,這一目的直到今天仍然適用。把握住這一規范內核,對“信息交換形式”的理解就可以與時俱進。在今天,“通信”的保護范圍應該擴展至所有信息交換和信息溝通的方式之上,包括早已經普及化的電話等通訊方式。互聯網的溝通模式改變了傳統點對點的溝通模式,比如電子郵件的群發乃至“信息群”的出現就是一種突破。這種溝通模式是在多人間、而非傳統的二人間進行。這也同樣帶來了問題,即此類群發的信息溝通究竟屬于私密性的“通信”范疇,還是公共性的“言論”范疇。
這就需要回到“通信”的本質功能。信息領域存在兩種不同的保護價值:一種是個人信息的獨立保護價值;還有一種是信息交換的保護價值。前者保護的是溝通前階段,涉及的是個人信息的自決權和隱私權,個人有權決定涉及個人的信息是否進入到溝通領域;后者涉及的是溝通過程,即對信息交換過程的保護。信息和通信這兩種保護領域,可以同時指向“隱私”,但這兩種隱私所保護的價值是不同的,其功能有所差別。通信雖然也是一種個人信息(如聊天記錄),但卻并非純屬個人事務的個人信息。通信的私密性,不只在于保障個體與社會的區隔,還在于保障溝通的順利進行。在歐盟的實踐中,通信與作為個人信息的元數據有所區分,通話記錄等屬于元數據,不屬于通信內容本身,但卻是個人信息(數據)的保護范疇。由此可見,“通信”的隱私功能與“信息”的隱私功能并不能完全一致。因此,可以將“隱私”類型化,進而對我國《憲法》第40條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出新的解釋。
2. 個人信息與通信的區分:通話記錄是否屬于通信
就通信的本質而言,通信應該是“信息的溝通與交換”,強調的是溝通的過程。《憲法》第40條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需要從保障“溝通”的角度來加以理解。這在教義學上具有雙重意涵:(1)通信的保護范圍得到擴展,隨著溝通技術的突飛猛進,所有屬于溝通領域的信息交換都應該納入“通信”的范疇,如短信、電子郵件、社交媒體的聊天等;(2)區分通信與非通信,將那些不屬于溝通領域的元素,納入個人信息的保護領域。就此而言,“通信內容”是屬于溝通領域的“通信”范疇,而通話記錄作為一種元數據,則屬于個人所擁有的一種信息,而非溝通本身,歐盟的實踐也證實了這一點。
這雙重意涵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現實中出現的問題,比如圍繞“通話記錄”是否納入“通信秘密”所產生的諸多學術爭論。杜強強將通話記錄比喻為信封,從而將之排除在通信秘密之外,納入隱私權的范疇,這一觀點建立在通信秘密與隱私權相區分的基礎上,對二者的限制在程度上存在差異,前者需符合文本規定的加重法律保留的條件,后者只需符合簡單法律保留的條件;張翔將通信秘密劃分為內容信息的通信秘密與非內容信息的通信秘密,對“檢查”進行重新解釋,將二者區別對待(主要體現在這一條款所要求的加重法律保留層面)。前者結論可以認同,但從教義學上看,通信秘密同樣屬于憲法隱私權的范疇。只是隱私存在不同類型,通信隱私與信息隱私之間存在著功能上的不同。后者的區分則存在解釋學上的矛盾,理由有二。其一,內容信息和非內容信息的區分難以成立,將“通話記錄”界定為一種“非內容信息”是一種誤解。通話記錄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內容”。事實上,并不存在無內容之信息,信息本身均包含有特定內容。其二,將通話記錄視為一種“通信”,納入通信秘密的保護范疇,但又將之與通信中的“內容信息”相區分,不僅有明顯違反憲法文義之嫌,導致體系違反的成本過高,而且不符合“事物之本質”,沒有看到通話記錄作為一種個人信息,與通信存在本質不同。此外,那種擔心憲法對于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所設定的限制門檻過高、過于嚴苛,導致實踐中公權力產生各種規避措施,甚至置憲法于不顧的觀點,一方面是對“通信內容”本身理解失當,錯將通話記錄等元數據當成通信本身,另一方面也未能看到,如果一旦在解釋論上敞開口子,放松對通信的限制,反而會導致實踐中進退失據,更容易為公權力甚至私主體過度限制通信大開方便之門。因而,應該回歸“通信”的本質,從溝通層面對之進行規范界定。
如果從“溝通”角度加以理解,就可以澄清“通信”的保護范圍,避免將通話記錄當成通信本身的錯誤出現。從這個角度,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憲法對于通信檢查所設定的嚴格限制,即必須要符合憲法文本所規定的三要件:國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作為檢查主體、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于通信限制的嚴格限定,其目的在于保證私下溝通的空間。私下談話應該是放松的,允許各種調侃、戲謔、夸張等成分,如將之公開,在失去語境的情況下對其審視,就會引發災難性的后果。“自由交談的特點通常是夸夸其談、臟話連篇、信口開河,這種反社會的欲望或觀點的表達,我們無須認真對待”,應該讓私下交流有充分自由的空間。
3. 數字時代的通信:交易還是私聊
雖然通信應與個人信息區分,定位于溝通,但并非所有形式的溝通,都屬于通信。在今天,通信的方式也已經發生相當大的變化,有一些溝通是經濟交易,而非私聊,其保護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互聯網中的社交媒體和各種即時溝通軟件層出不窮,許多軟件當中也都植入了溝通工具。比如在許多不以私密聊天為目的的App軟件(如交易平臺)當中,都具有聊天功能。但這些“溝通”的目的是實現經濟交易,在用戶和商戶、用戶和平臺之間出現問題時進行溝通,其目的是經濟性的,聊天功能則是附屬性的。對于這些“溝通”,就不能一概而論,統統納入通信秘密的范疇。應該區分是商業往來還是好友之間的私密溝通,比如很多交易平臺也設好友功能,用戶與用戶之間的溝通也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再比如,微信平臺的群聊,有一些帶有明顯的公共屬性(如工作群),而有一些則屬于家庭內部的私聊群。對此,也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視其私密性來加以區分。從私密性角度來說,個人和家庭的私密性是憲法上必須重點加以保護的,家庭內部的群聊同樣應納入通信秘密的保護范疇之中。
(三)兜底條款:一般隱私權的規范架構
在住宅和通信之外,還應該存在一個更為一般化的隱私的概念,作為一個兜底性的條款,從而能夠涵蓋除住宅和通信之外的所有隱私利益。住宅和通信之外,還包括私人事務的自我決定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私人事務的自我決定權包括生育權等。在數字時代,尤為重要的是個人信息保護權。我國在《民法典》當中規定了個人信息保護,并正在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但個人信息不僅要免受私主體侵害,更重要的是還要免受國家公權力侵害。個人信息保護不僅是一項私法權利,更是一項憲法權利。當前《民法典》所設定是隱私與個人信息保護的二分架構。涉及私密的信息屬于隱私權,非私密信息屬于個人信息保護權,使個人信息保護具有了獨立價值。《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并未使用“私密信息”的術語,而是使用了“敏感信息”這一說法。這表明,《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實際上是在模糊化個人信息與隱私的二元劃分。
前文已述,將隱私擴大為所有的信息之上,或者將隱私只限定為私密信息,都存在相應地問題。前者使隱私泛化,而失去其本質特征;后者則使隱私過于狹窄,無法適應數字時代信息化的發展。這就需要適度擴大隱私的范圍,從私密信息,適度擴展到與個人事務直接相關的信息方面,但已經完全公開化的個人信息則不在此列。這一范圍有賴于立法的形成,并根據社會情勢的變化,由法院在判例中通過解釋不斷予以補充。此種隱私向個人信息權的擴張,仍然保持了其本質特征,即在大數據時代盡可能隱藏自己的個人信息,實現對無法預知會產生何種后果的信息公開或讓渡的控制權,這也是隱私中“自主”面向的體現。
(四)憲法隱私權的動態保護和價值輻射性
憲法所規定的隱私的三種類型,分別對應不同的限制模式。結合憲法文本與隱私的社會功能,形成了一個隱私保護的層級結構。在此基礎上,對隱私權的保護,還需建立一種動態的規范體系,實現一種情境化的規制方式。在隱私保護方面,要考量的動態要素包括四個方面。(1)侵害主體。傳統來說,憲法只關注國家公權力侵害隱私的情形。但數字時代,個人對于隱私的侵害,甚至會產生更嚴重的后果。在數字時代,私主體(包括平臺)掌握的獲取隱私的技術更加強大,侵權后的影響會更大。私主體侵犯隱私之后的網絡公開,可能會導致一個人的社交死亡,并危及整個社會的信任機制。這就要求憲法通過對隱私的價值規定,對私主體之間的隱私侵害建立起一種輻射機制。(2)被侵害的主體。官員和公眾人物與普通公民在隱私保護上,顯然存在著差別,官員和公眾人物在相應的公共領域應該放棄一部分個人隱私。(3)私密性程度。并非任何對私人信息的公開都會導致對隱私權的侵害,也要視信息的私密性程度而定。(4)造成的后果。數字時代的網絡曝光,其后果往往是不確定的,這就需要結合信息曝光的后果綜合權衡。
除憲法所規定的針對住宅和通信的特別限制模式之外,對一般隱私權需適用《憲法》第51條的概括性限制。需注意的是,第51條的概括性限制在今天應受到更多學理上的重視,“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其中包含了私主體侵犯基本權利的可能性。在數字時代當中,私主體對基本權利產生了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強力的侵犯,并相較以往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后果。傳統上認為國家與私主體對基本權利侵害的不同在于,國家一旦通過立法、行政等方式侵害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就無所逃遁,且沒有其他任何的選擇權,只能被動接受。并且國家憑借其強制力,使得這種侵害具有直接效力。私主體則不同,其影響范圍具有局限性,比如某一網絡平臺對于用戶的禁言,用戶可以選擇其他網絡平臺,相較而言,公民仍存在一定的自主選擇權。因而在私法中,對這種禁言等行為甚至沒有干預之必要,嚴重情況下,也可以通過侵權法加以調整,而并無追溯至憲法之必要。但隨著數字時代平臺規模的發展,私主體的影響力開始有了顯著增強,比如對于公民社交而言,微信平臺幾乎是無可取代的,雖然微信的禁言、封號還可以通過新申請微信號的方式來挽救,但其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這就要求,在私主體之間的隱私侵害問題上,在適用民法規定的同時,還要考量隱私這一法益背后的社會公共性,即憲法中的價值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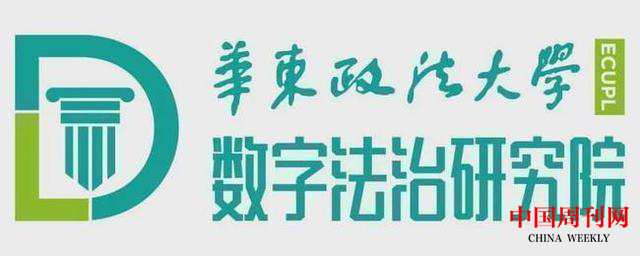
《數字法治》專題由華東政法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供稿。專題統籌:秦前松
編輯:海洋